【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1): 我在香港长大
前 言
上世纪70年代从香港移民新西兰的曼瑛博士是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首位华人女院士、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教授。曼瑛博士是新西兰华人历史研究的先驱,她的开拓性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曼瑛博士也担任许多社会职务,是位在新西兰社会备受尊重的华人学者。
我是2000-2001年在奥克兰大学研读影视传媒专业时,跨学科选读了曼瑛博士为期一年的研究生课程 – Chinese New Zealanders(《新西兰华人》)。这门课程是打开我认识新西兰社会和华人历史的一扇窗口,曼瑛博士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也让我受益匪浅。
毛传媒发表的对曼瑛博士的访谈系列,同原有的学术性访谈在内容和表述风格上有许多不同,内容更为丰富完整,表述也更为口语化。访谈录希望从一个高级学者的视点,展示新西兰社会这一百多年来的进程和华人移民在其中的命运起伏;同时也展示出曼瑛博士从事研究的心路历程和对个人身份定位的探索。
– 毛 芃

叶宋曼瑛博士2015年12月在自家小院 (毛芃摄影)
我在香港长大
叶宋曼瑛博士访谈(1)
在这一段访谈中,叶宋曼瑛博士谈了她在香港的早期成长经历,谈了在家庭影响所下产生的大陆情结。
毛芃: 请问您成长在什么样的家庭? 从您小时候的照片看,生活还是蛮不错的样子。
曼瑛:我算是生活在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我父亲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我母亲是香港汉文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这是香港当时唯一的一所师范学校。我父亲很喜欢摄影,水平还不错,经常参加沙龙摄影比赛,他喜欢给我和我姐弟照相。

曼瑛和弟弟
这一张照片我印象很深,我和弟弟拿的这个画报,其实是为了做反光板用,因为那时候的相机还没有闪光灯。
我们兄妹们都是念的官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私立教会学校学费都很贵,家里供不起。

曼瑛幼时同父母在一起
毛芃:记得您说过中学就读于香港的伊利沙伯中学,这是个怎么样的学校? 您还有印象吗?
曼瑛: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所男女同校(co-educational school)的中学,是所官立学校,就是政府出资办的学校。
伊利沙伯中学有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老师,校长也是英国人。他们有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
伊中是香港第一所有夏令营营地的学校,学生们在那里进行划艇、爬山等户外活动,夏令营里的路也是学生们自己建的。
香港传统的中小学教育偏重课本,不太注重课外活动。而伊中有救护训练、有童子军、歌咏队、乐队、辩论社;有篮球、足球队伍;还有戏剧演出、圣诞庆祝和新年舞会;学校还带学生参观机场、航空母舰、电影片场、天文台、矿场、天文台、立法局、报社。 可以想见,这些活动对学生的眼界、思维、对学生的活动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培养都有积极影响。

曼瑛(前排中穿裙子)读伊中学时与同学们参加露营、划船活动。
毛芃: 您在伊中的时候, 是学霸吧?
曼瑛:我不是学霸,因为我的数学太差了,不过我中、英文倒是很好。
我在伊中念了7年,这是我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价值观的形成、对社会的看法、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专业的态度和责任心,这些都是在伊中学到的。而最宝贵的经验是,我明白了什么是教育的最高理想。
我中三的时候学校分科,我被分到理科班。但我数学差,对文科兴趣更大。我同桌女学生被分到文科班,她其实更想念理科。我们于是去找老师,希望能对调。
我那时候也就十四、五岁,记得校长韩敦 (Mr.Hinton) 先生亲自见我,跟我详谈不念数学、改念家政的种种利弊。韩敦先生是英国人,很开明,很尊重学生的意愿。我改学了文科,我同桌学了理科,后来还去美国留学,学有所成。如果不是当年改科,我恐怕也不会进香港大学学历史,也不会有今天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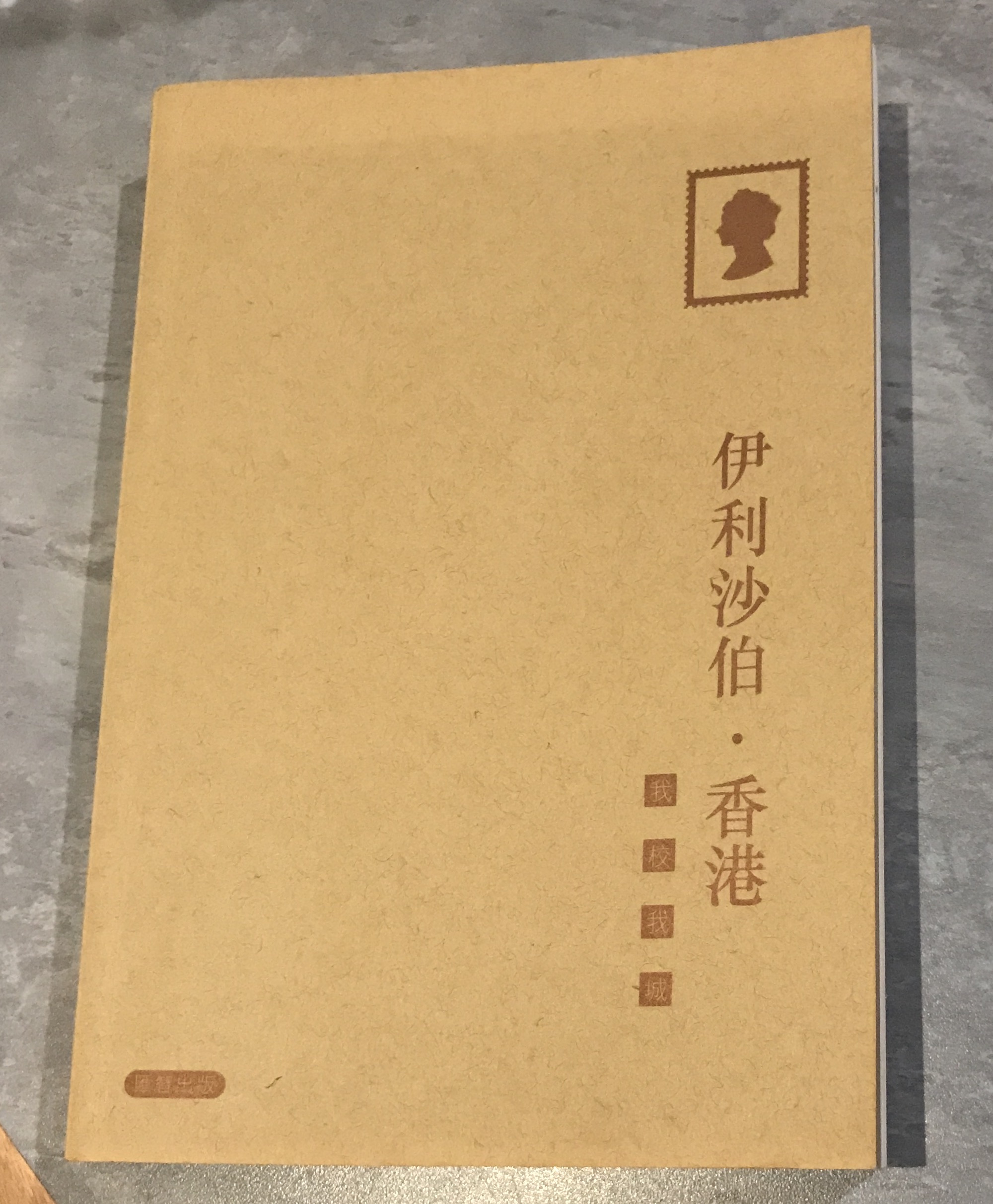
伊丽沙伯中学毕业生写的回忆母校的书(毛芃摄影)
在伊中的学习经历,会让我思考教育的终极理想,那就是应该为每个学生提供实现自我的可能性。
毛芃: 真是很羡慕你的中学时代呢。回想起我读中学时,各个学校都以升学率来考核,不要说课外活动,音乐课和体育课都取消了。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大家都是趴在教室写作业,我那时候是班上的文艺委员,记得有次心血来潮提议大家唱歌,结果班主任在楼上办公室听到了,下来一通训斥。我争辩说是课外活动时间。班主任说那就出去跑步,锻炼身体也比唱歌强。我们只好绕着操场跑步。
中学时一切都是为了考大学,除了升学几乎没有其他,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贫瘠的青少年时代。
曼瑛:伊利莎伯中学当时是比较特殊的。香港也是到了80年代,中学课外活动才慢慢普及起来。
毛芃: 您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大学了?
曼瑛:是的,中学最后一年是联考(Matricultion),香港是英国的中学教育体系,Form7后参加全香港联考,我考入了香港大学。
香港那时进大学比较难,因为只有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还是才建的,不像现在的香港有七、八所大学。
毛芃:当时香港是英语教学吧?
曼瑛:是的,香港当时实施殖民地教育,政府学校和教会学校是都用英文,只有中文学校用中文教学。
中学时,只有中文课和中国历史课是用中文讲,一星期四节。其他课程科学、地理等全部是用英文教。
香港是殖民地风气很浓的地方,学生在校都要求说英文。记得在香港大学念书时,上课当然是要说英文。就是下课教授不在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孩子也都是讲英文。那个环境会讲粤语也不讲,回到家才讲。
毛芃: 记得201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人来采访您,您讲过年轻时对大陆还是蛮有感情的。
曼瑛:对大陆的感受,嗯,我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从小就有很多困惑。我记得念中文课的时候,第一节课总是讲“我的故乡”,对故乡的描述是前面有河流,后面有荔枝树之类,同香港的环境很不一样。那时的香港到处都是石屎森林,没有什么有特色、有美感的建筑。
我就问我妈妈:“我们的故乡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叔父、我的祖父,都是在香港政府工作,用香港话来说就是“打政府工,铁饭碗”,是很好的工作。那我就想“我的祖父为英国政府工作,这不是汉奸吗?” 我这么去问我妈妈,结果被她严厉教训了一顿,我印象很深。
我后来写我们家的家史、家谱,还到香港政府档案办公室查找资料,查到我祖父是什么时候进入政府、做什么工作、多少薪水。他那时候是政府高级公务员。
怎么样看历史、看中国,我其实挺困扰的,心里很多问号。
当时挺困扰,现在也有点困扰。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孩子,到底自己是什么人呢,真的是很不清楚。
当时我的父亲、叔叔都蛮爱国的,爱中国。1941年, 日本侵犯香港的时候,他们都逃到内地去,逃到桂林、重庆。当时的年轻人都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吧,我父亲对中国挺有感情的。我记得他订阅中国出版的刊物,一本叫“Chinese Reconstructs”的杂志,就是 《中国建设》,说中国怎样怎么样好,同香港的说法很不一样。

英文《中国建设》杂志 (网络图片)
那时候香港的孩子是过4月4日儿童节的,那是国际儿童节。 但是我爸爸带我去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活动现场,那是香港的左派人士组织的。我发觉这是不同的世界,氛围完全不同。香港当时是小康的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而中国那时经济还没有起步,两边很不一样。
所以,很早我就想到底我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什么地方,有点困扰。
毛芃: 香港左派组织举行六一儿童节活动,这很有意思,您还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吗?
曼瑛:不记得是香岛中学还是培侨中学,总之是很左派的学校。

曼瑛在香港著名的天主教堂St.Teresa Church
毛芃:记得您说过在香港时还听大陆电台节目?
曼瑛:是的,中学时很向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我记得晚上听得特别清楚。就是想听一下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也许想追求一些深刻的什么东西吧。
那时候的香港不像现在,现在香港电台的节目怪严肃的。 我们从前那个时候,电台节目我觉得就是风花雪月的东西,没有启发性,没有什么深度,因为香港那时候只讲赚钱。当然也不是说这样不可以。
毛芃: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父亲半夜三更听台湾广播,记得是叫《三家村夜话》。大人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躺在被窝里偷偷听,也听不懂,就记得主持人的声音很慢、很柔。
您会同你的同学、朋友们讲你听大陆节目吗?
曼瑛:不会,那时候香港人不谈政治。那时候很多香港人连国货公司都不敢进去,很怕的。 香港60年代就有国货公司。
不过我会同我的兄弟姐妹们讲,同他们谈论。
我们当时是个大家庭,我的父亲和几个成家的叔叔们都在一起居住,十来个堂兄妹们在一起玩。那时候大家主要靠阅读报纸获取信息,我母亲给大家订阅了各种报纸,从右派的《星岛日报》到左派的《大公报》都有,因为我的叔叔们有的观点左一些,有的右一些。
我们孩子们也跟着读这些报纸。同样的事情,左派报纸一个说法,右派一个说法,我们从小也就习惯了人们对同样的事务有不同的看法,也学会了比较、学会了分辨,兄弟姐妹们经常讨论各种问题,通过辩论表达自己的观点。
虽然香港那时候是殖民地,没有民主,但自由还是很充分的。
毛芃: 您小时候习惯不同的声音,我小时候倒是习惯一种声音,因为全民都要统一思想。不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为什么会对您有吸引力呢?
曼瑛:我那时觉得香港是很肤浅的、很没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社会。
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香港到处都在建高楼大厦,很多建筑工人在建筑地盘工作。看他们做很危险、很辛苦的工作,站在竹子做的架子(俗称竹棚)上,那时候也没有劳工保险。我就觉得香港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一些人生活得怪舒服,可是另一些没有升迁的机会,他们的生活很悲惨。
我那时对大陆的实际情况也知道的很少,就是看看英文的《中国建设》杂志。
那阵子,很多香港人,例如我大学的同学听到“中国”就很怕,不会去接触。也许我因为我爸爸的关系,对中国没有那么抗拒。我爸爸他们也不是说中国有怎么怎么好,但是对大陆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感或者说排斥。
(本文所有曼瑛博士的黑白照片都由她本人提供)
(未完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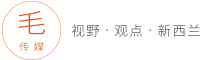




天气好好-周小舟: 很有意思和深度的访谈,好像一个盒子不同的面,我们在同一段时空中,却有迥然不同的感受和体验,期待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