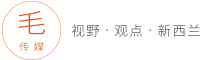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Yeehah】寻找顾城梦断之所-山林中的海景木屋

(奥克兰 ) Yeehah 图 / 文
“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
—-顾城的诗《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生于1956年9月24日,属猴,天秤座 性格:神秘,性感,具有艺术天分和音乐才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意,人生变化起伏很大,但意志坚定,可以获得成功。优点是具有独特的风格及魅力;想追求的目标会坚持到底。缺点是非常霸道、专断,具有相当的叛逆性,精神非常紧张。
顾城,生于1956年9月24日,属猴,天秤座 性格:神秘,性感,具有艺术天分和音乐才能;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意,人生变化起伏很大,但意志坚定,可以获得成功。优点是具有独特的风格及魅力;想追求的目标会坚持到底。缺点是非常霸道、专断,具有相当的叛逆性,精神非常紧张。
20多年前一位中国诗人之死让新西兰这座小岛名扬中国和世界。1993年10月8日,中国著名朦胧诗代表诗人顾城断魂新西兰奥克兰市附近的度假胜地急流岛(WAIHEKE ISLAND)。诗人本命年受尽煎熬,37岁生日才过几天,杀妻自缢。
20多年来,诗人之死倍受争议。经过很多年我才搁下诗人杀妻之恶名,重新思考悲剧的背后。绝顶的天才往往生活中多是白痴或疯子。世人过誉海子,多责顾城,中国人更以为天才必完美无暇。天嫉英才,顾城之死未必是他可以选择的。右脑高度发达、活跃 ,做事经常不被多用左脑的大众理解。天才不需要被美化,美化圣人、天才、伟人,是愚人的冲动。天才对常人本来就是一种反常的缺陷。我们的时代很不幸,好歹出了几个半疯半傻的天才。
“我喜欢东方宁静致远,也喜欢西方富于自我的、有童心色彩的观注和体验,这一切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我几乎处在一个疯狂的边缘,那时候我惟一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停止思想。如果我在想下去我就要疯了。离开中国以后我到了小岛上去,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 《筑一个小城》栗子采访

顾城每日眺望的海湾 ROCKY BAY
度假胜地急流岛(WAIHEKE ISLAND)被中国人习惯称“顾城岛”,距奥克兰港或半月湾港40多分钟的船程。岛上的居民近万人,20年前大概才一半。多集中于西部,遍布葡萄酒庄和度假别墅。顾城住的小区位于中南部半岛山林区,东接岛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近眺翠绿的乱石湾。
探访顾城故居是多年的夙愿,今得闲遍游全岛,踏访计划终于实现。从游客最集中的奥尼洛瓦镇驱车东行,山路崎岖蜿蜒,20分钟后驶过跨河长堤,便进入半岛的密林区。一条弯路进出,而狭窄的山路盘旋而上,若不小心看路,在山中兜多少圈也未必找到那条原本应该被顾城诗粉磨光的林街。

僻静的小街
转悠了很久,几乎迷路。终于踏上这条半山上的小街,面东南,绕山而建,林繁叶茂,阴凉僻静,路上无车无人,住宅掩映在丛林后。停车后方听见阵阵蝉鸣。走进上坡车道,右手一处闲道杂草过膝,尽头树丛凌乱交错,若不是当中立块中文警示牌,谁会知道只是举世闻名的“凶宅”所在。面对禁区警告,我犹豫了一阵。按诗人的知名度,故居当远远超出私宅的意义,何况此宅被废弃20年,无人居住,是名副其实的鬼宅,诗人亡灵若徘徊与此,定万分寂寞,应不会介意偶尔有人冒然探访。
差不多20年前(1994年),南岛本(Bain)家凶杀案轰动全国,警方一周后毫不犹豫地烧毁了本家凶宅。顾城的旧宅算是幸运的。20年闲置却依然保留至今。虽听说邻居多避谈命案,还是比较宽容。也许得到亡灵的庇护,究竟能苟存多久,恐怕只有听天由命了。
“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性——分类判断、因果辨析??;他是在一瞬间以电一样的本能,完成这种联系的——众多的体验,在骚动的刹那就创造了最佳的通感组合。有一次,我看到太阳——新鲜、圆、红、早晨等等一连串的观念和直觉一瞬间一掠而过,直接到达了草莓——甜而熟的草莓;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句诗:‘太阳是甜的。’
“诗人不仅发现那些最具象和最抽象、最宏观和最微观、最易知和最未知之间的联系,而且,他还不断地燃起愿望的电火,来熔化和改变这种联系,有时,他几乎把这样的火焰布满人间,直到他所创造的世界呈现出天国或地狱的本相。”
–《关于诗的现代创作技巧》

幽静的车道,应该是20年前的老样子
步入旧车道,好像离死亡、离诗人、离过去更近。钻出遮蔽车道的灌木,眼前一片凄凉凋敝的惨景。一段残破的灰色挡土墙默默无语,被杂草乱枝包围。地上一堆发锈的铁板。哪里有房子?哪里有上山的小径?
迈过铁板,仔细观察才发现被爬地植物覆盖的石阶。趟着荒草,一步步登上潮湿的台阶,不时拨开墙一般的枝叶、蛛网、荆棘,引得山蚊蛾虫乱飞。荒径向左拐,终于看见一座两层残破不堪的木板方屋。
故人远去,万木凋零。墙上的漆一半已剥落,却能看出原色。藤蔓爬满紫红木墙,几乎要吞噬整个破房。青苔在阴湿的处画着苍老的颜色。部分玻璃窗被木板封死,脸凑近贴在模糊的窗上,隐约看见屋内放满木框门板一类杂物。完全看不出住家的模样。仰头见二楼两扇紧闭的木窗,玻璃映出午后的蓝天和匆匆掠过的白云。不知哪扇窗曾让诗人追云心动。在屋的两侧寻找上楼的通道,但无路可循。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
早晨,阳光照在草上
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
— 《门前》
房子四周被灌木丛包围,通向房后的路堵得死死的。两侧巨树遮天蔽日。没有读书声、吟诗低唱、吵架、哭泣。只有“阳光照在草上”,一下子“关掉世界的声音”,一片死寂沉沉,听着自己脚压踏野草的唦唦声,时深时浅,忽忽悠悠,好象不是自己发出的声音。带玻璃的木门上钉着块醒目的英文警告牌:“私宅!!!!!请离开!!”表示现任屋主对不速之客的反感。旁边的玻璃破开一个口子。墙根挡板几个黑洞足够野猫野狗进出了。

“第一届青春诗会,当时我在会上呢?就说了一点儿我的想法。我那个时候比较天真,先说我们中国人怎么老问吃饭没吃饭呀?怎么谁也不问我快乐不快乐呵?这就是一句傻话那时候;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一去,人家就问我“你忧郁吗?”我就哭笑不得了。反正我说了一席话,我当时的说法呢,就是幻想就是幻想,现实就是现实,这两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幻想是天上的云,随风飘荡;而人就同地上的猪狗一样,你就飘荡不得;然后我说呢,如果作为云看待世界呢?国徽跟瓢虫呵,就是那个“花大姐”呀,是一样的,也许感觉花大姐更好看哈?我说了这话呢,好几个在场的前辈就走了,柯岩没走,她说顾城你留下!我就坐在那儿,她说我告诉你,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你知道那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给我吓了一大跳;我那时才知道,那话是说不得的。”
–《人生如蚁而美如神》德国之声亚语部采访
在房前的园子里转了一阵,几乎放弃上楼的念头。拨开右侧的密叶,通向二楼木台的小径已被乱草覆盖,无路可循。钻出树丛,残旧的木楼梯引向一处很大的木平台。平台上爬满细蛇般青藤,木条长满黑酶点,踩在上面支支呀呀,感觉随时坍塌似得。我只得象猫一样小心翼翼地挪步,感觉自己就象只饥肠辘辘的野猫。阴影的背后躲藏着目光如炬的“黑色的眼睛”。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
—《墓床》
平台前方蓝天和海,迎面的木条墙涂成紫红、黄、绿三色。旧漆翻卷开,露出几层颜色。紫红色的漆刷到一半,要遮盖绿色。男人怕戴绿帽子,所以对住宅上的绿色特别敏感。破烂木门也带玻璃,里面用灰白窗沙遮盖。“黑色的眼睛”盯着我。最大的窗子一半被木板钉死。一幅现成的油画,一首褪色的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顾城那天是不是从这扇门追出去,杀妻后失魂落魄地回屋,又恨恨地冲向那棵绝命树的。这扇紧闭了20年的门,讲述被遗弃、被疏离、被遗忘、被冻僵的绝望,和被埋葬的孤独。

“海笑了
给我看
会游泳的鸟
会飞的鱼
会唱歌的沙滩
对那永恒的质疑
却不发一言 ”
–《规避》

原本挂在屋檐上雨水槽横在门前,变了形堵住门口,青藤沿着墙根往门上爬。站在二楼的平台上,平静的乱石湾就在眼前。是什么搅乱了诗人的心,让他疯狂。孤独,绝望,寂寞、懊悔、嫉妒、失落、贫穷,还是突如其来的背叛,惨败的沮丧?20年来几乎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除了“黑色的眼睛”,人们似乎忘了他写过好多灵光四射的诗篇。
“不要睡去,不要
亲爱的,路还很长
不要靠近森林的诱惑
不要失掉希望 ”
–《回归》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
“让阳光的瀑布
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
它拉着我
用强光的绳索”
–《生命幻想曲 》
“‘我被劫了’
我对太阳说
太阳去追赶黑夜
又被另一群黑夜
追赶”
–《案件 》

银芦向空宅招手
“万卷藏书不救贫”。贫穷历来是折磨诗人的魔咒。从但丁到惠特曼,杜甫到陆游,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煎熬。陆游有多首诗坦抒穷困潦倒的心境:“减尽腰围白尽头,经年作客向夔州”《九月三十日登城门东望凄然有感》; “自笑谋生事事疏,年来锥与地俱无”《自笑》。骨瘦如柴的放翁跃然纸上。
顾城对金钱的概念、谋生方式近乎儿童的水平。他曾讲:一想到生计,脑海里便有万条毒蛇。顾城好歹有一处安身之处,却终日被贫穷的恶梦缠绕。靠近平台的边缘,无凭栏可依,往下望深不可测,只见翠绿的茂密丛林,不见人家。仿佛归隐深山。一切简化,净化,几乎没有选择的苦恼。但要能扛得住寂寞。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是安心的地方就是家,家是一种心境。在新西兰我有这种感觉,离开了新西兰我还有这种感觉。我可以想念我过去的地方,遥远的家。我很少做外国的梦,差不多每天一闭眼就回中国去了。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北京,回到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而醒来,则在一个破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想念很重要。只要你有这种想念就可以安心——四海为家,又可以在家中走遍天下。
“舒适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东西,鱼在水里舒适,鸟则在天上;那个岛对我合适,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感觉,也没有人说太多的话,更主要的是没有什么事可供选择,不选择多好!
“我们到岛上的那天晚上,在黑暗里点了一根蜡烛,外头下着雨,湿气渗进来,我们坐在蜡烛下。我心里想,从十二岁起,我准备了二十年,这回我可得逞了。我的妻子没说话,她一定恨死了。”
–《筑一个小城》栗子采访
不选择多好!”是顾城真实的内心表白。可人一辈子不论怎样折腾,其实就做一件事:选择。什么都离不开选择,命运是随选择而变的。拒绝、害怕、逃避选择的人是痛苦的。最不喜欢选择的人,往往总是被逼着选择。人生中最难的选择莫过于生死的选择。

诗人的姐姐顾乡在《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详细叙述了诗人最后的岁月,有很多大段对白。除非当时录音,否则不太有可能完全真实记录当时琐碎冗长的对话。多处讲到谢烨谈论死的问题,态度冷漠令我不寒而栗。对白不长,上下呼应,我相信是可信的。中国女人训夫时的杀伤力有时超出想象。但在生死问题上决不能当儿戏,尤其对诗人。
1:(顾城)近乎自言自语:“死在这事儿上的人也不少,蝌蚪死了,××也自杀过…… ”
“可是你不死啊!”谢烨生冷的几个字又吓了我一跳。话居然能说到这个程度上!“你着什么急呢?”弟居然还那么安定地说:“我还有事想做,—-”
2: (谢烨)“我让你死,我能让你死吗?你不死,谁能让你死!”
3: 弟笑了下,对我说:“谢烨特逗,跟我说:‘要死,你就写完书再死。’”弟说完,脸停在一种傻子样的笑上。
我吓了一跳。
烨不满地:“哎,说清楚了,这是好话坏话?”然后对我道:“他老是死啊死啊的,要不他真早死了。”
“他死不了,你放心。”烨用颇为不屑的口气说;“×××都说:他说死又不死。都知道他要死,可是他不死,他不死人家怎么办?”烨脸绯红。我一时都听傻了,—–。”假如上述的情节属实,这些话每日打磨人性之剑,每一刺都刻骨铭心。
“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验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
– 《河岸的幻影》
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对每个口无遮拦的女人都是警示。我不是要将顾城疯狂的主因怪罪在谢烨头上,只是提醒活着的人,不管对多么熟悉的人,千万不要拿死开玩笑,特别在本命年。死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对身心俱焚的诗人来说,绝对不是最后的选择。 
远眺,摆脱窒息
20年前的那个下午,一切都结束了。 童话从那一刻开始凋谢枯萎。走下破烂却保留基本点旧貌的平台,好象屋里的人刚刚离开,惨剧刚刚发生,就在附近,在丛林里消失了。“这个过程,是一个文化人的诞生,也是一个自然人的死亡的过程。”
诗人是文化人中最反常的一群人,疯疯颠颠,疯言痴语。天才的诗人更是疯子里的精品。当今的时代很难出大诗人,因为人们太正常、太平庸了。如果顾城活在网络时代,必为活跃的网络诗人,开博客,玩微博,粉丝几百万,“泰囧”之娱如此而已。
“在语言停止的地方,诗前进了;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关于诗歌创作》。结束,才是开始。
同代摄影家肖全在他的书《我们这一代》中,记录了当年顾城等诗人被诗迷爱戴的狂热程度,远超过超女的粉丝:
“(诗歌朗诵)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诗人们被保安人员疏散在后台的一间化妆室里,门被反锁,走廊外人声鼎沸。
一小时过去了,人流有增无减,保安人员只得抱着一堆各式笔记本,请诗人们一一签字。两小时又过去了。坐在化妆桌上的顾城面色铁青:我不管,我要出门,我要出去!
他一把拉开门,气势汹汹地往外闯,诗迷们见顾城出现了,欣喜若狂蜂拥而来,他却用胳膊肘左右开道,杀出一条‘血路’。”

穿出树丛走下山坡,抬头回望,孤零零的破木屋背着阳光。告别一个时代,诗人的黄金时代不再,告别那些永远活在诗的黄金时代里的诗人们。
天才的诞生也许是上帝不小心犯的错误。难怪顾城自嘲:“诗人不过是个守株待兔的人。经过长久的等待,他才发现,自己就是那只兔子。”于是他象只兔子一溜烟地逃到新西兰,逃到孤岛上,一头撞到那棵树上。

谁呀?吓人!

沉默的窗口,永远睁着眼睛。


顾城当年栽的桃树果实累累,每年春定桃花盛开


曾经快乐、惬意的地方

封闭的门,将所有的记忆藏在里面

回头最后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