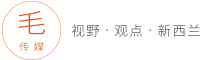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郑永年】什么样的批评可以增加知识?
针对不同的观点,人们如何回应?
可以从杨绛先生和吴建民先生过世,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反应,来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讨论官方的反应)。因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几乎会写几个字的人都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以假设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两位先生,只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新闻媒体报道等“认识”他们。甚至很多人连他们的作品都没有看过,而跟随别人作评论。
从民意的角度,这个群体也很重要,但从知识的角度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如果意识到大多作比较严肃的评论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可以从中看出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和对知识的态度。
这种反应也可以延伸到重要的政治人物,如秦始皇帝、朱元璋、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等。当然,政治人物和杨、吴两位先生不同,前者是决策者,可以影响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因此人们对他们的反应不可避免地更情绪化,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应也可以延伸到学术界称之为“社会事物”的东西,例如社团、企业、政党、宗教等等。社会事物本身并不产生观点,但因为它们原先是观点的产物,因此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反应,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对知识的态度。
杨、吴两位都是社会名人,去世之后,有积极评价的,也有负面批评的;有歌颂的,也有诅咒的。不管怎样的评价,大都可以置于两个非理性的极端。大多数人只是想表达情绪,都会尽力罗列各种证据来支持其情绪。“情绪性反应”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他人、不同的观点、社会事物的主要特征。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知识界和社会为什么产生不了有效的知识;为什么知识进步很慢,甚至没有进步。知识(这里不涉及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知识,例如宗教)是因为观察社会而产生,因为批评而进步、增加和发展。中西方对人和事物有不同态度和反应。
法国从拿破仑时代始就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从高中开始进行“三段论”教育方式,学生不能对人和社会事物只表达接受还是反对,更不是歌颂或者诅咒,而是要提出正题和反题,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新论题。这个传统在古希腊就有了,到今天仍然是西方(至少是学术界)对人和事物反应的最起码的态度和方法。

中国的理性思维传统
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理性思维传统。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派都是理性的,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基于这些现象之上的概念和理论来生产知识,并和其他学派交流和争论。汉代的《盐铁论》还能看出法家和儒家之间的理性论辩。但是之后理性论说越来越衰微,情绪论说越来越张扬,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字不能表述理性思维,而是表达情绪的最有效言语。(这种现象有人关注过,但没有人深入研究。)
近代以来,情绪论说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堕落到互相怒骂、人身攻击、戴帽子、比谁的声音大甚至暴力。今天因为社交媒体使用等因素,似乎又一个高峰到来了。
情绪不可避免,但没有理性的运用,情绪转化不了知识。数千年了,对人和事物的看法仍然停留在情绪,没有知识的增加和进步,更没有新知识的产生。至少对那些想追求知识的人们来说,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为例,他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大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发明了很多思想性概念,例如“退出、发声和忠诚”“激情和利益”“不均衡发展”等等,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试以他在1991年的《反动修辞学:悖谬、无效、有害论》(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所概念化的“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为例,来讨论西方学者如何面对不同观点去生产和增加知识。
根据他的观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不仅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着竞争和斗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也一样。近代以来世界发生大变革,不断出现很多社会事物,例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和从前的社会事物大不相同,甚至是前所未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面对巨大变革的理念,如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公民理念、普遍公民权运动所揭示的民主化和社会福利理念,不同的社会群体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关切的是保守主义者用什么方法来为其“反动思想”辩护。
在赫希曼那里,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反动派”或者“反动思想”都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客观中性的概念,就如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种力量一样。“Reaction”实际上是“反应”的意思。中文普遍翻译成“反动”也恰如其分,因为人们总是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称为“反动派”。“反动派”在中国是一个极其政治化的词汇,无法用来理解赫希曼。强调这一点对知识生产非常重要。
对社会科学来说,知识的生产首先不是道德问题。一旦具有了道德的预设,就会对知识生产构成制约。德国社会学者韦伯说社会科学家观察社会现象,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价值中立”。不过,在知识产生之后,知识对社会发生影响,那时再给知识“道德判断”,那是另外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因为知识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历史上这些反进步的“反动思想”所攻击的目标,虽然有些是针对民主政治,有些是针对社会福利,但就思维结构来说,它们都包含着共同三种论证结构,即“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悖谬论”的逻辑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或者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即知识的边界),改革只会带来和目标完全相反的恶果。“无效论”的逻辑是:社会发展自有其逻辑,人类的改革措施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有害论”的逻辑是:改革虽然可能是好的,可是会摧毁其它更重要的价值。
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批判
赫希曼以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批判为例做说明。“悖谬论”认为,社会福利只会带来更多的穷人和更大的贫困;“无效论”认为,社会福利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因为贫困是人类社会必有的现象,无法以人为的努力消除;“有害论”则认为,社会福利摧毁了其它更重要的价值,如个人自由。同样,“反动思想”对民主政治的攻击也包含着类似的三种观点。
赫希曼发现,尽管“反动论述”都同时包含这些共同主题,但是针对不同的进步运动,在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些主题受到特别的关注。例如针对法国大革命,“反动运动”的主题主要是“悖谬论”,即认为,推翻帝制的大革命所带来的不是平等和自由,而是更残酷的政治压迫。
针对普及公民权的运动,“反动论”者最常用的论点是“有害论”和“无效论”,前者论证大众民主和自由的不相容性,后者相信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是少数精英统治,民主化并不能改变这个现象。针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攻击,“悖谬论”重新获得重视,即认为,为了消除贫穷,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贫穷;政府的救济措施取代了传统家庭制度,导致对政府的更大依赖。
赫希曼在书中并非只讨论“反动”论述的基本思维结构,也讨论了进步思潮的类似错误。例如,当“反动派”的“有害论”认为,人类的某些价值是不相容时,进步派则认为,所有好的价值都能相辅相成,所有的理念都可以成功地实现;当“反动派”的“无效论”认为,人不能改革社会运作和历史进程,进步派则倾向于认为,历史毫无疑问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掌握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方向。
作者不是在形而上学层面来讨论问题,而是考察进步和反动双方如何发展他们各自的论题(知识体系或思想)。作者所做的不是价值和道德评判,而是在形而下层面所做的经验分析。西方自近代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基本并没摆脱这些思路。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或者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自由派),尽管他们所发展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也具有深厚的价值观,但双方都是从经验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自文艺复兴后,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少人会诉诸于宗教、道德或者其他形而上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社会科学理论就是经验理论。即使是规范性理论,如果没有经验证据支撑,就没有合法性和说服力。理论和思想的经验性至为关键。经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是各派建构理论和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各派能够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这些基本事实使得各派理论和思想不会走得太远,从而实现讨论和争论过程中的理性对话;并且理论和思想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促成理论和思想的进步与和现实的继续相关性。

反观中国,遇到“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情况,中国学者会像赫西曼所讨论的那样,去做严谨的逻辑思维吗?大多反应都会落入本文开头所讨论的情况。人们对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情绪反应,很能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的缺失的状况。如何克服情绪思维而确立理性思维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