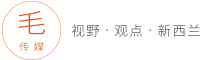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评论】美式民主与中式专制此消彼长 自由主义的出路在哪?
勇敢的乌克兰保卫者被誉为不仅是为他们的祖国而战,而且是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战。我们被告知,这是一场为我们而战的战斗。
在这种说法中,乌克兰是21世纪之战的原点。美国总统拜登将其称为专制与民主之间的较量。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场战斗到底是为了什么?
民主?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它不讨人喜欢,媒体受到束缚,反对派被噤声或被监禁。普京被形容为一个新的沙皇。但是,他确实是选举产生的。
美国本身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民主的堡垒。上次大选陷入了谎言和阴谋中。特朗普的支持者非但没有和平交接权力,反而洗劫了国会大厦这一美国民主的所在地。
在其他地方,民主已经成为政治强人、民粹主义者和煽动者的牺牲品。他们在分裂和统治的平台上通过投票箱获得了权力。
十多年来,全球的民主如自由落体般坠落。每年,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少。
与其说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专制本身在民主中获得蓬勃发展。
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更准确地说,民主的捍卫者谈论的其实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民主理念,它声称个人主义、自由、人权和法治是主要的美德。
理论上看起来是不错的,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也没有被证明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攻击。
自由主义有时被认为是一种战斗的信仰,但在面对暴政时,它也常常因为胆怯,甚至同谋,而被轻易嘲笑。
在批评者看来,自由主义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一股没有意义的辞藻的洪流。
德国法学家、曾经的纳粹分子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嘲笑自由主义是“无休止的对话”。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称其为“辩论社”。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说它使人变得“懦弱”。
成为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什么
在21世纪,自由主义如同民主一样正处于危机之中。它到底代表着什么?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命运,从危机到胜利再到危机,徘徊不定。
自由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那场血腥恐怖的回应。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它受到了战争、革命、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攻击。
当时和现在一样,自由主义者问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自由主义能否抵御暴力的挑衅而自己不变得暴力?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困境”,即若要保持对自由主义的忠诚可能令自由主义失败。
政治学家乔治华·切尔尼斯(Joshua Cherniss)在他的新书《黑暗时代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in Dark Times)中接续了伯林的话题。
他指出了这种困境的核心:自由主义者要面对不确定性,而专制主义者却没有任何怀疑。引用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话说:
“最好的人缺乏所有的信念,而最坏的人却充满了激情。”
“最坏”的人相信历史会屈服于他们的意志。所谓历史主义,就是认为人类被设定在一个方向上,暴行会得到原谅,以便将我们送达这一命运。这可能是一种世界末日式的观点。
历史主义之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说,“历史是一个屠宰场”,我们每个人都在上面被牺牲。
正如切尔尼斯所说:“历史被认定为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净化道德转变的故事。”
自由主义被发现是不合需要的,它坚持人道社会的美德,但正如切尔尼斯所写的,它未能“认识到政治的现实”。
正如他无情地指出:“当自由主义者珍视文明和纯真梦想时,大众在呻吟,世界在燃烧。”
可以被救赎吗?
切尔尼斯的著作不是为了埋葬自由主义,而是为了救赎它。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他指出了几个人物,他们在黑暗的年代里,说出了一个不同的自由主义。这些哲学家和作家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困境。
他们看到了自由主义的弱点,但也看到了自由主义者有可能用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成为独裁者来对抗独裁主义。
切尔尼斯说这些思想家提供了一种“有节制的自由主义”;“一种对自由主义的缺点和缺陷的认识”。
有节制的自由主义者接受了不确定性,摒弃了简单的答案,但仍然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正如切尔尼斯所说,他们以一种“精神”来对待政治。切尔尼斯说,残酷无情的解药“可以在培养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中找到”。
它是一种在价值观感知下的存在方式,但不是固定或永恒的。切尔尼斯说,这些思想家寻求“分歧和矛盾”。
切尔尼斯引用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话,将有节制的自由主义定义为“不在于持有什么观点,而在于如何持有这些观点”。
另一位是法国作家加缪,他认为公共辩论的质量和风格对自由主义的成功至关重要。加缪的自由主义“以谦虚为标志”,平衡“各种要求和各种极端”。
加缪著名的小说《瘟疫》(The Plague)讲述了一种大流行病重创了一座城镇,因为人们都处于封锁状态,作为专制主义的一个寓言。
他挪用了西西弗斯的神话,即被诅咒永无停息地把巨石滚上山,但巨石又会重新滚回山底,以此来回击历史主义的确定性。
加缪在确定性中看到了危险。他写道:“我们在那些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人中间感到窒息。”
他曾对马克思主义有过短暂的兴趣,但最终驳斥了其“最终性”的想法。加缪最终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
切尔尼斯承认加缪并不赞同自由主义的观念,但他提供了一种避开绝对主义或狂热主义的温和态度。
不过,这并不是一种寻求平衡或解决之道的节制,这不是一种针对“不温不火的灵魂”的自由主义,而是“炽热燃烧的心灵”。“适度但不轻微”,这是一种勇敢面对极端分子并设定限制的自由主义。
加缪等人是在革命、战争和迫害的烈火中锻造出来的。他们努力在黑暗的时代找到光明。
是自由主义失败了,还是自由主义者失败了?
在20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往往成为舒适者的专利,被精英们所俘获。
它演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对社会的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沦为傲慢和胜利主义的猎物。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通过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宣布了“历史的终结”,即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最终目的地。
福山现在与自由主义的最新危机作搏斗。在他的新书《自由主义及其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中,他承认自由主义受到了来自政治左翼和右翼的攻击。
他说,在一些人看来,自由主义是 “一种老旧的意识形态,无法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
但福山仍然是一个信徒。失败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主义者本身。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自由主义,而不是更少。
其他人,如哲学家朱得思·施克拉(Judith Shklar)在1950年代警告说,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道德内核。它被有权势的人用来对付无权无势的人。
这就是施克拉所说的“恐惧的自由主义”,即故意“施加痛苦……以造成痛楚”。施克拉采用了一种并不拒绝自由主义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想向长期被压制的声音开放。
现在怎么办?
在乌克兰战火纷飞且中国的威权主义又挑战民主之际,自由主义在哪里?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声音,那些有节制的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否还对我们有教诲?
切尔尼斯说,现在“流行的是为自由主义的陨落而欢呼,且加入抢夺残骸的行列是有利可图的”。
他说,我们再次被那些“相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人所窒息;我们再次站在人性被激怒的一边”。
西方对自己的信心不足,共同点也更难找到。而专制主义者以肯定的态度呈现自己。
切尔尼斯说,这就是“说着伟大语言的政治强人”的魅力所在。
他说,我们需要道德抵抗和坚韧力。我们需要拥抱“英雄般的雄心”,正如施克拉所说,“不是武装分子的勇气,而是可能受他们所害者的勇气”。
在乌克兰,我们看到了勇气。乌克兰人很可能只想着生存,而不是为我们所有人拯救自由主义。
但是,当枪声最终沉寂下来时,乌克兰人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会想知道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