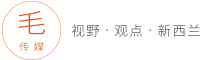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小刀随笔】二姐丁香
当喧闹退去露出忧伤,谁在深夜咀嚼凄凉。
我也尽量使自己的文字清香,画意悠长,应了姐姐那份文艺的渴望,圆了姐姐褪色的梦想。
— 弟弟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家庭孩子比较多,老二总是容易被疏忽的。她不像老大带来第一次的惊喜,也不像老小受到宠欢。如夹缝中遗漏的阳光,谁在意了她的思想?谁在意了她的着装?她在忽略中成长。
比如二姐,丁香。
就名字而言,丁香是很美且富有诗意的;但假如你生长的地名就叫丁香,那这个名字是不是起的有些随意了呢,我想二姐曾经应该很讨厌这个名字的。

我想二姐应该跟我一样,是没见过丁香花的。我也不知道丁香镇名字的来历。我们小时候住的老房子,据说是政府从地主那没收来的,很大,空荡,楼板黄旧发白,被人流传闹鬼的楼上,我是从来不敢上去的。
有天井的厅堂,雨落的时候,水注从避尘处倾下,溅在下方的大青石板上,注入两旁的水池里,隐隐的水光荡漾在四面厢房的壁板上,而池中的水却永远不会溢漫。
望着天井上方的天光,二姐会拼命忍着磕睡连连,摇晃着摇床,希望幼时的我早点进入梦乡。
“经常迷糊中把摇床摇翻,把你扣在下面,头上鸽蛋大的包,害怕爸妈骂,涂半盒清凉油,巴望消了。”
“还有吃饭有点好吃的菜都在你碗里,我就在拐角哄你啊,宝宝,给姐姐尝一口,就尝一口。”
姐姐每次说起过去趣事,自嘲中总能听到一丝心酸。
只是我是不记得这些的。我拿着父亲的帐簿到野外画村庄,跟小姐在小河大河里摸鱼虾,拿着缠着蜘蛛网的竹圈去粘蜻蜓,这些事情都不记得有二姐。奇怪她在哪里呢? 直到忽然有天听到姐姐谈恋爱了,才知道原来二姐一直静静地静静地就在大家身旁,悄悄地悄悄地花儿开放。

二姐的男朋友就是我的英语老师。印象中,他一开始是跟学校另一老师的女儿谈恋爱,怎么又成了姐姐的男朋友?我百思不解。可因为是我老师,我还是很欢欣的,而且他还很帅。
二姐当时在镇上财政所上班。他们怎么开始我不知道,只知道父母很反对,似乎我父母对每个姐姐谈恋爱都反对。于是聪明的英语老师想到一个办法,每晚上我家来给我免费补习英语。这样一举两得,既讨二老欢心,又拉拢未来小舅子,关键是可以有借口来见女朋友。
在亲爱的英语老师的努力下,我的英语水平上升到非常好的程度。
但是浪漫的时光肯定不会是陪我在小房间里探讨英美帝国主义的语法的,总得两人花前月下。只是每每姐姐迟归,总挨父母的骂。父母每晚临睡时, 总把前、后、偏门都拴好,反正你在不在家,都别出去或进来了。只是前脚父母睡去,我便偷偷地把后门拴拨开,好让约会的姐姐回家。
可惜,美好的爱情并没如我祝愿那样走到最终。
多少美好的姻缘都在“我们当时太年轻”中错失了。

伤心的英语老师一怒之下,借酒意撕碎了姐姐保管的几大本税票,那是非常严重的工作失职,父亲花了好几个晚上,一片片的补贴粘好。碍于父亲的脸面,才避免姐姐被辞退的后果。
带着满心的伤痛,姐姐被调到更偏远的乡村。
更多的夜晚,父亲坐在院落,默默望着葡萄架上的月影,夜深秋风凉,担忧胆小嬴弱的二姐在远方。
我去看过姐姐,那时我已经去城里上学了。财政所环境还好,只是异乡人生不熟,到了晚上同事下班回家,剩下姐姐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关门睡觉,紧闭门窗,孤独警觉,让我难过。于是我跳在城里学的霹雳舞给姐姐看,读写的诗给姐姐听。
姐姐满心欢喜,告诉隔壁乡邻“这是我弟弟”。我想,姐姐那时开始为有我这个弟弟感到骄傲。
其实二姐是很喜欢文艺的,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她穿着绿军装,在公社的小舞台上演唱“样板戏”,不论是《红灯记》中的铁梅,还是《白毛女》中的喜儿,二姐都唱得有声有色,韵味十足。
但我能陪伴姐姐的日子毕竟短暂,何况我也是寂寞的性子。大抵记得龙应台的话:“亲爱的,难道你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财政所对面是林业站,站里有户和善的人家,对姐姐很好。
大娘经常送些好吃的过来,但来得更勤的却是大娘的儿子,叫毛毛的小伙子。
父亲不久就调到城里去了,更是牵挂二姐,他奔波找人想把姐姐调到身边,只是还没有办成就太过匆忙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二姐嫁给了毛毛。落脚在这个小山村。

而我多年后接触到的丁香花,却是素有“丁香王”之称的画家曹辅銮所画的丁香。曹辅銮画笔下的丁香柔美典雅,似乎总在不经意间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充满诗意。
是否也可以形容心目中的姐姐呢?

曹辅銮作品
现在的姐姐似乎过得肆意潇洒,但谁会又知道,当喧闹退去露出忧伤,谁在深夜咀嚼凄凉。
自父亲离开,我们姐弟也就象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洒落四方,各自坚韧地生长。如果不是太贫瘠的土壤,谁又愿甘心失落最初的梦想。
我也尽量使自己的文字清香,画意悠长,应了姐姐那份文艺的渴望,圆了姐姐褪色的梦想。
姐弟啊,也只是这一生而止,血浓于水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