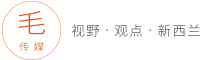孔捷生: 沈从文与汪曾祺
汪曾祺曾对我说:文学有大家与名家之分,名家通常就是要比大家写得好,但大家毕竟是大家,名家毕竟是名家。 沈从文与汪曾祺这对师生,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大家是谁呢?想必是鲁迅。诚然他的文笔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再者鲁迅在文学上虽很有建树,却也非大得吓人。然而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深深刻痕,却唯有“大家”才能有那种力度。只不过,若说鲁迅的小说写得比沈从文好,实难服人。
作者: 孔捷生

周有光112岁生日那天,他感叹:“上帝把我忘记了”。次日寿星公即仙逝。
妻说这句话不能讲,说出了上帝就记起他了。我却觉得蒙召上帝是美事,是一种诗意境界。李白醉捞明月,骑鲸而去;李贺梦见绯衣人乘赤虬传诏,玉帝修成白玉楼,召他去撰记,此为玉楼赴召的典故。二李羽化升天都很奇瑰,周有光前辈庶几近之。
周有光前辈我无缘见过,但见过沈从文,他们是连襟。张家“合肥四姐妹”分别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作家沈从文、汉学家傅汉斯。
1980年初,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同学都是各地新锐作家。晚上无事我们会出去走动,不时去看望文学前辈。当时所长是丁玲,她只来讲过一次课。我不喜欢她,觉得她的面相、眼神、语言都很凌厉,我从未登过她的门。
沈从文没有给我们授课,他1949年后已远离文学,再也不碰了。那晚同学古华说:“我们去看看沈从文前辈。”我太迷他的小说散文了,尽管当时文坛还在冷藏他,但其文学魅力却无人能及。能见到他实在荣幸,我们二人便去了。那年头北京全無夜生活,昏黄灯光下的街道甚为清冷。沈宅在历史研究所宿舍楼,楼梯幽暗,但一进沈家就觉得温暖。沈从文和古华都是湘籍,他不单未见过我,连我名字和作品都不晓得。沈从文前辈却认真地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沈夫人张兆和还用笔记下来。
古华说到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沈从文听得很耐心,但没有插话。那晚沈前辈没有和我们谈过文学,甚至他谈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了,只有一种印象难以磨灭,就是两位前辈儒雅谦和的儒贤气质。我们两人刚参加过1979年末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沈从文的名字被人提起,他的回应是:“我只是出土文物。”这句话在我们作家同学中传为奇句。我告诉沈从文前辈,他只付之一笑,笑得淡然泰然。
在京进修期间,我见过不少文革落难的文学前辈,但复出后眉宇间依然有一种势能,那是新中国文坛赐予他们或宠或辱的徽记,尤以丁玲为最。但沈从文完全没有,他俨然从民国穿越而来的文化人,纤埃不染。1988年沈从文辞世,最后遗言是“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
很多年后,听闻文坛争说诺贝尔文学奖最初打算给巴金,老舍儿子又言之凿凿说已决定给他父亲,但公布前老舍下世了,诸如此类都子虚乌有。巴金长寿,要给他有大把时间。至于老舍,绝无可能。先不论其作品,我亲耳听马悦然说过,五七年他在北京,看到和听到老舍的反右文章和言论。真正已决定得奖人选是沈从文,其后瑞典文学院才知道沈从文已去世几个月了——这并非后来哄抢失落桂冠才传出的轶闻,而是1985年我和北岛访问瑞典时就听马悦然说的。
由沈从文又说到汪曾祺,他在西南联大时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之骑鹤西去也很有故事。
1997年汪曾祺先生去世了。人总难免有一死,只是他去得匆忙了些,七十七岁在如今已难称高寿,他的同辈好友作家林斤澜活到八十六岁。后来才从古华文章得知,美食家汪曾祺刚从泸州回京,泸州大曲想必喝了不少,他入厨制作了一碟萝卜丝以清润肠胃,不巧一条萝卜丝呛进气管,好象是引发内出血还是什么的,总之抢救不及……我想,汪曾祺之死,也和先朝那两位大诗人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当年常居北京,与汪交往颇多,亦曾几度结伴远足,若干花絮,我偶尔在文章中提及。汪曾祺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大家与名家”之说。
汪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闻一多是他授业老师,但我常听他提到并满怀敬意的尊师是沈从文。闻一多“有一句话说出来点得着火”的炽热气质,与淡泊恬退的汪曾祺不相符,他笔下之飘逸空灵,颇得沈从文真传。
这或许正是他之“名家说”的由来。汪曾祺曾对我说:文学有大家与名家之分,名家通常就是要比大家写得好,但大家毕竟是大家,名家毕竟是名家。
沈从文与汪曾祺这对师生,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大家是谁呢?想必是鲁迅。诚然他的文笔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再者魯迅在文学上虽很有建树,却也非大得吓人。然而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深深刻痕,却唯有“大家”才能有那种力度。只不过,若说鲁迅的小说写得比沈从文好,实难服人。
汪曾祺的名家说,令我茅塞顿开。李杜是大家,小李杜是名家,李白几乎不写七律,杜甫很少绝句。李商隐和杜牧二者皆能,瑰丽,灵动,精致。词坛苏辛是大家,但就纯艺术而论,比起李后主孰高孰低?
我想,二者区别在于——大家传诸后世的是不朽宏篇,名家传诸后世的是千古绝唱。
汪曾祺另一些轶事,值得一提。西南联大当年学运汹涌,汪却是笑傲书林的消遥派,又非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的那类死啃书本的学生,他自谓当年不参与学运,仅因看不惯那些“党干”学生领袖,身为组织者,事发时总是让热血澎湃的青年学子去与军警叫阵,领袖们都在茶馆里泡着,静候“反独裁”捷报佳音。以汪曾祺个性,他讲的一定是实情。于是,他一直不与中共党团组织沾边,哪怕后来在江青垂直领导的“样板团”里,他也无意要求“进步”。
然而,1986年汪曾祺还是向京剧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80年代恰是胡赵新政的黄金时期,又有朱厚泽来大谈"宽松",大家心情舒畅,是自然的。很不巧,他参党之日赶上“反自由化”,此事被拿来登报宣传。我一直没机会探问汪老之初衷,况且这种事又不象文学话题那般可放言无忌,他与我并非同辈,哪能推心置腹到这份上?或者,个中因由只有他的好友林斤澜先生才知其详。
汪曾祺与我们几个辈分不同的朋友同游川陕,曾到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监狱旧址一走,高墙上“洗心革面”、“回头是岸”的斑驳大字犹依稀可辩,却觉得要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高压威慑话语要软性许多。
汪老寻寻觅觅,认出了他蹲过那间牢房,不过当日并非国民党将他投入此处,而是江青将他们几个《红岩》创作组的成员塞进去“体验生活”的。本来我们有幸瞻仰第九出样板戏——《红岩》,却终于胎死腹中,关于此戏的来龙去脉,汪老自己曾撰文专述,兹不赘言。
总之,人在旅途,大家聊天时不免话及《沙家浜》剧组旧事,令我印象至深的是,多次见过江青的汪曾祺并不墙倒众人推,硬去编织“女皇”花边丑闻,他眼见为实,说从未目睹江青有何失仪之处,江对他本人一直十分客气。除了他觉得江青驾临样板团视察时那作派有点造作,其他实在说不出什么来,甚至他在向江青陈述剧本的修改时,也没觉出此妇人盛气凌人和颐指气使。这和江青已被固定化的脸谱出入甚大!汪曾祺无意去颠覆历史,他只是不愿人云亦云罢了。
后来又读了李志綏的书,大略明白江青并非随处放刁撒泼,她平时待人接物的斯文,还要远胜汪东兴之流的土包子。江青此人,你只要敬鬼神而远之,就无足为患,你要和她作对,又或巴巴的往跟前凑,都有大麻烦。汪曾祺仅系一介书生,又是非党人士,更无意顺着竿子往上爬,如浩亮、刘庆棠等名伶,那才真叫自找!然而,那年头要洁身自好,并不容易,这便是汪曾祺了。
做名家,并非靠文笔空灵典雅。再读《边城》,又读《大淖纪事》,魅力泉眼源自作家那份云水襟怀——这就是沈从文和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