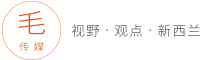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一)

中国现代史是支离破碎的,有些碎片恐怕早已“丢失”,留下了大片的空白。或许是有人有意而为之,以为消磁、删除、抹去记忆便可平安无事。他们不知道历史是人类的财富,是前人的经验,也是后人的借鉴,记住历史这个民族才更成熟,忘记历史这个民族永远长不大。 – 穆迅
(一)
我的妈妈从小就爱唱歌。她唱了一辈子。
妈妈十四岁时应该说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她长得好看,聪慧活泼,天生一副好嗓子,就跟着红军去打鬼子,于是到了延安。不久就成了部队的主要演员。

妈妈出身在山西太原。我小时候她总说,她的妈妈也长得漂亮,不但写得一手好字,刺绣也是远近有名。她的爸爸长得英俊魁梧,在政府里做事,她是家里的“掌中宝”。
可是就在她的妈妈三十多岁的时候,得了肺病早早去世了。她的爸爸于是很快为她找了个继母。她觉得继母不但没她妈妈好看,而且为她爸爸生了个弟弟,对她越来越不好,于是她有了要离开这个家的念头。正好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太原,她跑去亮开嗓子就唱,部队就把她带走了。
我当然没有见过我的姥姥和姥爷,连妈妈以后也再没见过她的父亲。据说姥爷曾经到部队去找过她,说她太小了不能参军,可她回家后又跑回部队。一位文艺队的领导吃惊地看着眼前浑身是土的女孩说,这丫儿可是有个性。
延安,这是妈妈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决定命运的地方。她觉得最美的是位于西边的凤凰山麓和东南方向的宝塔山。那个长方形条石砌成的城墙作为屏障证明了延安自古就是打仗的边塞要地。当然不久城墙就被战士们拆了去修礼堂,延安的大小礼堂有五、六个。妈妈最喜欢那条由北向南静静流淌的清澈的延河水,大家天天用延河水洗脸,然后提一桶水给炊事班送去。开始妈妈被分配到抗大学习,她穿上部队从国民党那领来的军装,戴上青天白日军帽。她还学会了打草鞋,裹綁腿,每天除了学文化,就是立正敬礼,跑步练操。
妈妈在女兵班认识的第一位班长,比她要大十几岁,大家都称她“老大姐”。老大姐最大,妈妈最小,所以妈妈格外受到老大姐照顾。看到妈妈的军服太长,老大姐给她缝进去一大块;看到妈妈还拖着山西带来的两根小辫,老大姐给她剪成短发;看到妈妈总爱把两鬓的短发掖到耳后,老大姐就把自己的一个榆木小镜子送给她。妈妈在部队找到了家的感觉,她说老大姐很像她的妈妈。
因为妈妈嗓子好,很快又被送到“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一边学习一边演戏。老大姐对她说,进了大学就是大学生了,不能老是活蹦乱跳。
以后,妈妈知道鲁艺的校长是毛泽东,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周扬,何其芳,陈荒煤常去给他们讲课。
不久,妈妈她们开始排戏了,她很快成了“女一号”,“女一号”每演一场就能得到一个煮鸡蛋。在战争时期演出最常发生的事是“导演”根据抗战形势经常在演员临上台了还在改歌词,妈妈总是一转眼就把新词背下来上台就演因此深受大家喜爱。
在妈妈八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看过她自己写的一份简历,当时她在延安主演的小戏剧小歌剧不下三十多出。
妈妈是演《兄妹开荒》“走红”的。
《兄妹开荒》演的是兄妹俩人响应“大生产”和“学文化”号召一边锄地一边学认字。
两人一边唱一边扭相互考看谁认的字多,整个表演把学文化的意义宣传得通俗易懂。妈妈只要把嗓子一亮,立即获得满堂喝彩。从此妈妈有点骄傲了,早晨不愿起晚上常迟到。部队纪律是很严的,因此妈妈常受到批评。
有一天妈妈又要上台了,这时老大姐急急忙忙对着她耳朵说,毛主席今天来看演出。妈妈还没反过神来后台音乐响了,她挎着个篮子就上场,一边唱一边用眼睛往台下瞄。她看到毛主席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因为眼睛走神,结果词唱错了,台走错了……
后台导演急得捶足顿脚,老大姐安抚了这个又安慰那个。结果妈妈接受了严厉的批评,她把在延安学会的所有的字都用上写了平生第一份“检查”。
随着前方战事越来越紧张,为了给战士们鼓劲,妈妈她们的学习时间越来越少,演出越来越多。她天天晚上上台,和大家一样用碳灰画眼睛和眉毛,用庄稼糜子碾碎了抹成红脸蛋。妈妈总是一边化妆一边背导演改的词,她的妆也总是比人家画得好看。
妈妈不但戏演得好,还天天跟在老大姐身后,不是种地就是纺线。她开始学会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再累再苦早上按时起,集合不迟到。演戏不马虎,劳动不落后。她好长时间没有写“检查”,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一年后,老大姐做介绍人,妈妈成了全班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不久,妈妈发现每天晚上总有一个男人靠着小礼堂门口看她演出。他个子高高的,表情温和肃静,文质彬彬,聚精会神。
那天妈妈和老大姐还有几个女学员到操场散步,看到十多个男兵在打篮球。篮球架是用老乡家夹木杖的棍子支起的,让村里的铁匠弯了两个铁圈。当时妈妈看到其中有一个大个子跳得非常高,他每次投篮即使球没进也带起一片叫好声。妈妈此时屏住了呼吸,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个大个子,他姿势矫健,英俊威武,跳起来再落地时显得动作潇洒干净利索,不大的球场成了他展示身姿和球技的好平台。妈妈认出来了,他就是天天来看她演出的那个男人。
后来妈妈和他认识了,原来他是从上海那边来延安的大学生,当时任延安一张报纸的负责人,他让妈妈管他叫“E君”。
E君天天按时来看妈妈演出,如果有一天没来妈妈就焦虑不安。后来每天演出完后E君都留在门口,等妈妈卸了妆两人一同去散步。
自从认识了E君,妈妈只记得宝塔山上的塔楼披着霞光非常美丽,窑洞微弱的光也变得明亮。妈妈对我说E君特别喜欢到河边走走,所以延河水最能证明她和E君的相爱。
五十年后我去过延安采访,好奇心驱使我先去看延河。浑浊的延河水几乎成了“黄河”,河面狭小,河床布满黄泥。想起当年在这里谈恋爱的妈妈心里倍感酸楚。当年妈妈爱听E君说话,他讲历史故事,讲名人回忆,讲文学,也讲他的报纸。他很少讲战争,讲苦难。
认识E君以后妈妈变得平静了,矜持了,可也经常被E君的话逗得前仰后合。E君送给妈妈一块丝绒缎子布料,他说是从上海带来的家人让他留着做被面。妈妈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布料,细心珍藏起来。有一次E君说他喜欢听妈妈唱歌,于是妈妈向着河水唱起“延安颂”。
我记得妈妈八十多岁了还唱这支歌,前面四句她总是唱得很深情: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柳影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妈妈和E君的相爱很快在部队传开了。有一天老大姐匆匆赶来把妈妈叫到外面,她从来没有那么严肃过。她说妈妈不能再和E君来往,这是组织决定。
“可是我们没有影响战斗”。
“这是纪律”!
妈妈赶紧找到E君,她的声音是颤抖的。
E君只说了一句:一场暴风雨要来了。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