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是中国的教师节,询问几位奥克兰朋友对他们对班主任的记忆,他们的回答都很精彩。
穆迅:想起中央美院附中最后的班主任—-温葆老师
温葆老师就是画“四个姑娘”那张画的作者(见上图)。这张画列西方美术史中中国文革前的代表作之一。小矮个,童花头,笑容可掬,娓娓道来。曾来奥克兰半年。至今仍有来往。
我从小就不会和领导搞好关系。嘴也不甜。又不幸撞見的班主任个个都平庸、一本正经。只有温葆老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其他的班主任,哼哼,全视我为反叛,落后生。差点被整成反动学生。
李蕴: 班主任都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班主任有小学的,中学的 所有人都在我记忆中。小学严老师说过:大家一起上一辆电车,但每个人的目的地都不一样。我记忆犹新。
中学文革学校让大家批判我爸爸编剧的电影,同学们都等着看我怎么写。最后班主任王老师宣布我的批判文章分数最高。我当时就知道老师保护了我,终身难忘
远洋秋枫:永誌不忘李老师
李老师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不是李老师,我现在可能是农村低保户。
我是穷山僻壤的山里娃。李老师是教代数的,除了教课育人之谆谆不倦外,对我似乎有格外的关怀,我八岁父亲便离世而去,我在李老师的身上感到了父爱的温暖。
说来话长,桩桩件件细说起来,不是这一微信容纳的了。揀二三亊畧表,足可见师恩浩蕩。
头一件,我的代数三年都得一百分,这其中除了我的努力,当然更有李老师的心血,常常给我额外辅导,岀难解题练习攻关。
第二件,因了家贫无力升学,李老师主动提出他可以适当予以补贴,但终因如洗的家境而无法如愿。李老师和几位同学竟送我十里路程,而后师生相拥,洒泪而别。
第三件,离校后两个月,当时政府部门,到学校招聘人员,而我己经回到远离学校六十华里的农村。是李老师亲自为我办妥了所有手续,甚至包括体检。然后让教导处写信通知我回校报到。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信件到村已有些时日,加之信放在村公所无人专管,我未能能及时收到;幸亏看门的大叔发现,送信到我家。打开一看报到限期只剩两天。我二话不说,揹上行李赶往学校。招聘的人员已经带上应聘同学走了。
教导处告我,是李老师向招聘工作人再三联系,多给了我几天宽限。我和另一位请假迟走的同学,去省城报到。一个山里娃,走上了工作岗位。
我牢记着李老师的嘱咐,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多多读书,不忘学习。我读书读书再读书,孜孜不倦读书学习,以此感恩老师的教诲,以此丰富我的人生。而今年纪虽老,但我永远是一个不辱师命的的学生,在各位老少朋友面前永远是一个小学生。
李老师已离我而上天堂,我要用我学习的态度,让老师在九天含笑。
山高水长有时尽 唯吾师恩日月长。
Yeehah: 班主任姓杨
小学班主任姓杨,她是我记忆中最厉害对我最凶的老师,所以我能记住她的名字。
几乎每天不被她羞辱,训斥,罚站,留校,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反常。最让我奇怪的是,她有年请假生孩子,我居然梦见她,还哭了。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她为啥那样恨我。每天一副更年期的脸孔,没听过一个字好听的。凭我怎样努力,做好事,装乖,红领巾跟我无缘。直到小学毕业典礼那天,凶巴巴的班主任赏赐我和几名“落后生”入队,让老子这辈子只带了半天红领巾。
我时常想念那几位对我体贴关怀的老师:王晓淑,叶多佳。她们是革命时代的阳光和天使。可惜没有她们的照片。
爱与恨,对儿童来说终生难忘。小女今年刚好与当年的我同龄,每天放学快乐兴奋,几乎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我有时想,人能耐再大,生错了时代和地点,又能怎样哪!
珂珂:小学时正赶上文革
小学时正赶上文革,到乡下捡麦穗,我们那个漂亮的班主任被男生在脖子衣领里放了一条小青草蛇,结果大叫一声就昏了过去,住了两周的医院才出来。那时候学生就是这么折磨老师的,回想起来真的不是滋味。
(毛芃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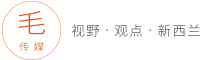




穆迅:还真找到这张画呀,谢谢!这是温葆老师在中央美院的毕业创作。随后分到附中做我们毕业班的班主任。这是她的第一任。三十年后她居然还认得我,记得我的名字。从此有了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