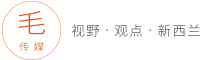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 (六)
红色的回忆:
我的妈妈爱唱歌(六)

我在冰冷的东北农村一边战天斗地一边在心里担心着妈妈,不知道她怎样照顾自己,眼前总闪现她脆弱、忧伤和慵懒的身影。不久我请假回城,得知爸爸住进了“牛棚”.继母一个人在家着急,她劝我去牛棚看看爸爸。我说服了造反派好不容易见到爸爸。他比以前更瘦了可精神不错,微笑着和我开着玩笑。爸爸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反右,现在又经历“文革”。他历经坎坷但心中始终留守着自己的大气坦荡,在风雨中净化自我领悟生命,是我终身的榜样。规定的时间到了,造反派催我走,在门口爸爸忽然小声问我:“妈妈怎么样?”
我一时慌乱,不知爸爸指的是哪个“妈妈”,当然是继母。我说,“她很好,惦记你呢。”
“你妈妈怎么样?”
“我,我刚从农村回来,她应该在五 · 七干校吧。”
爸爸知道“文革”这么乱,妈妈肯定不会安静的。
果然,我打听到妈妈竟然从干校自己跑到北京,又一次把腿摔折了。我急中生智竟然在妈妈老战友那打听到消息,妈妈竟一个人跑到北京八宝山去看E君去了。她居然能找到E君的骨灰。“文革”期间没有鲜花她便折了几根树枝放到了E君的身前。八宝山在北京的西边,回来时她一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唱一不小心摔倒在马路牙边将左腿骨折。
她被人送进医院没有人陪她没有人给她送饭,我在农村她又联系不上,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样熬过来的。后来她被送到一个老战友家,老战友还在挨批,他的夫人也是延安过来的,二话没说收留了妈妈。
我好不容易联系上妈妈。天冷了,妈妈让我把她的衣服寄往北京。那天窗外风雨交加,我在妈妈的箱子里发现了她的一个化妆盒,打开看里面躺着一个很旧的本子。我好奇地掀开第一页,看到一个男人的像片——他面目清秀轮廓分明,静静地看着你。粗粗的双眉下有一对温和的眼睛。他就是E君?我的心呯呯跳。
像片显然是从很旧的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六寸见方,颜色呈黄绿色。我耳边出现了幻觉,好像听到一个庄重而有分寸的低沉嗓音,那么富有变化地表达着什么,像是远处暴风雨无穷无尽的雷鸣。
我惊慌失措,注意到像片后面贴了一张红纸,两边各留出一块一寸宽的红边,用毛笔竖着写了两行字:右面是“我亲爱的战友”,左边是“你在何方”——这是妈妈的笔迹。
这两句词我很熟悉——歌剧《江姐》里的两句歌词。那是江姐在得知她的丈夫彭松涛牺牲的消息后唱的一个经典片段。怪不得妈妈平时拿着歌本一遍又一遍唱。
天昏昏,野茫茫
高山苦城暗悲伤
老彭啊
亲爱的战友
你在何方……
你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响
谁知你壮志未酬身先亡……
在我得知妈妈的故事之前,听妈妈唱这段歌我觉得她唱得很深情,很优美;知道妈妈的经历以后,听得出她唱得很凄苦,很失落,很忧伤……
自从我被“判”给妈妈后,爸爸每月给我三十元“抚养费”放在妈妈那里。这一天我到继母那拿到下个月的三十元钱,坐上火车去了北京。
妈妈见到我像见到了大救星。她的腿还打着石膏。她没有告诉我因为什么摔成这样,我什么也没问把她接回了东北。
在以后的漫长时光里,我再也没有离开妈妈。可是因为工作太忙,我不可能承担起服侍妈妈的重任,再说我天生也不会做家务。这时“文革”结束了,各家可以顾人了,我开始为妈妈找阿姨,这一找就是十几年。妈妈也不愿让我为她影响工作,只要我总能出现在她眼前就行。
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可她精神状态还好,而且和邻里、单位的人也处得不错。我慢慢观察,只要不刺激她,不让她烦躁,她是不会闹的。但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每天我不把药放到她手心她是绝不睡的。这让我很恼火,因为这样吃药等于慢性自杀。
我上网,查医药书,始终找不到能让妈妈少吃药的办法。她吃药太多不但经常出现幻觉,而且敏感,多疑。有一次我看到她的大米旧了,便给她换上新的,半夜她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偷她大米了。电话把丈夫和女儿都惊醒了,女儿发牢骚说姥姥怎么不管天黑天亮就打电话。还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向妈妈借了一个钢丝床,半夜妈妈又打电话命令我把床必须马上给她送回去。我穿上衣服顶着月光打车送床,给生气的妈妈盖好被子,轻轻哄着她睡去了。
这样的事不知发生了多少,慢慢成了家人互相传说的笑话。每次家人埋怨时我总是一句话:她是病人,她是病人。对于病人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无法向大家解释也什么都解释不清。
大夫给妈妈开的药越来越多,而且药和药自相矛盾。吃了心脏的影响胃,吃了胃的影响肝。吃这个不能吃那个,那个不吃这个吃了一样犯病。看着妈妈桌上站着一排排药我真是一筹莫展。于是我仔细研究每种药的说明书,严格掌握妈妈吃各种药的时间,我想尽办法减轻妈妈的痛苦,哪怕只有一点也行。
最难的是妈妈住院,几乎每个月我都要送她去住一次院。其实妈妈很怕住院,她的血管已经很难进针可吊瓶从来就没停过。有时刚住了几天她不耐烦了半夜跑到院子里大喊大叫,无论阿姨护士谁也拉不住。于是不管是黑天白天我经常被医院的电话叫过去处理妈妈的事,只要我往妈妈身边一站,她很快就安静了。
有时候我真的被妈妈折腾得烦了,我在心里叫着,爸爸呀爸爸,你离婚拍拍屁股走人了把妈妈甩给了我,你知道我受多少罪吗?可一看到妈妈身体好一些安静下来时我又心软了,我们又说又笑,所有的苦恼都丢在了脑后。
妈妈高兴起来像个孩子。也许因为是演员出身,她说话幽默反应极快,常把周围的人逗得哈哈笑。不论是剪头发的小姐还是做按摩的师傅,哪怕是小卖店的大叔饭店的服务员都喜欢妈妈光临。只要妈妈一走进来,屋里顿时一片欢腾。我以前只知道妈妈爱唱歌不知道她竟这么风趣,她如果没有病该多好呀!
从那次以后,妈妈从来不提E君的事。直到她去世后我在收拾她的遗物时也再没有发现E君的那张照片。妈妈平时倒经常提起爸爸,她说爸爸其实是最好的人。
最叫我难办的是她想弟弟快想疯了,天天催我给弟弟写信。可是我无法说服远在南方的弟弟,他和妈妈几十年没见了已经非常陌生。我也没有权力强迫他来见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有他的选择。
我曾经暗示过妈妈小时候打弟弟的情景。她根本记不得了。
可弟弟却一直记着,并一直不愿原谅她。
后来我发现妈妈一到外面见到人就夸我,说我是电视台的高级记者,说我做了十年的省政协委员,说我得了多少多少国家奖,说我这个说我那个……这些话她都快背下来了。我奇怪妈妈为什么老向别人说这些呢?仔细观察发现其实妈妈内心非常自卑。单位里她资格最老工资最低,入党最早房子最小。妈妈的单位是省文联,别人都是作家戏剧家,她那么早的“当红演员”现在只是个老病号。
于是我安慰妈妈说,别看你现在没成就是因为你身体不好,你看你至今歌声不老。你看你拿来歌谱就能唱词,这个本事我还是跟你学的呢。我甚至说别看你女儿有能耐若不是你剖腹生我我还不知道在哪呢。几句话说得妈妈哈哈笑。
1992年春节,父亲在北京突然病逝。我没敢告诉妈妈,将她交待给阿姨带着女儿进京奔丧。继母很伤心,她和爸爸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从来没红过脸还生下一个妹妹。“文革”中她陪爸爸一起下乡喂猪种菜。没有她爸爸很难活下去的,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后来妈妈在报纸上看到了爸爸的“讣告”。我非常紧张,后悔自己忽略了报纸。妈妈还好,她只是叨咕说爸爸是好人,再就什么都不说了。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妈妈把她心中的压抑和痛苦都发泄到爸爸身上,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可是爸爸对妈妈又了解多少呢? 这对我始终是个谜。
没想到五年后,弟弟在深圳突然心脏病发作也去世了。这对于日夜想念儿子的妈妈无疑是要命的事,我只好严守一切信息通道,我只能一直瞒到底。我绝不能让妈妈再受任何刺激。
妈妈没有意识到她身边真的只有我一个亲人了。我不能让她感到孤独,她只要提出任何要求我都尽量去做。在她过完八十岁生日后她说她还是喜欢北京,她希望晚年能在北京多呆些日子。我马上同意了正好北京我也有个家,说走就走。
记得那天在机场妈妈兴奋得手舞足蹈。她虽然老了但眼睛还是那样美丽,细细的眉毛依然舒展在两边。她的皮肤永远这般洁白细腻,一头银发更增添几分姿色。虽然难以发现的皱纹优雅地浮现在两个眼角,却遮不住她作过演员的气质。她说话使劲时还是爱用手习惯地往前一劈,有点像首长作报告,令我忍俊不禁。她的腰一点都不弯,只是那条摔伤的腿留下了后遗症,平时不得不拄根拐杖。此时她坐在轮椅上昂着头挺着胸新奇地看着周围的人。
北京,这是妈妈生我的地方。妈妈告诉我当年的王府井是什么样,告诉我当年我上的幼儿园的地址,告诉我她工作过的电影局……她就是不提八宝山。
还要不要带妈妈去寻找E君的墓呢?我脑子里闪了一下。精神脆弱的妈妈经不住任何刺激的,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链接: 红色的回忆:我的妈妈爱唱歌(1-8)